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心理学正在迅速从边缘走入中心。从社交平台到日常对话,越来越多的人用“原生家庭”“MBTI人格”“NPD”“高敏感体质”等词汇描述自身状态。这些原本属于诊室的专业术语,如今成为了人们理解痛苦、讲述自我的通用语言。
中国的“心理热”并非一蹴而就。从1990年代《知心姐姐》式的大众启蒙,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层面对心理干预的认可,从“积极心理学”的流行,到近年来描述疼痛、创伤和内心挣扎的心理语言的兴起。
“自我”成为思考单位,并非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如人类学者张鹂所言,“自我”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概念。在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个体往往被嵌入社会角色中。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才开始带着“自我”的眼光探视周遭,国家在社会保障中的退出,也带来了责任的个体化——心理语言,开始成为理解痛苦、寻找出路的替代性支持系统。
“心理热”既是文化现象,也是一场社会变迁的折射。界面文化发起“探秘中国心灵”系列报道,尝试从多个维度审视这场心理热:它如何进入我们日常生活,又如何塑造我们的感知和经验?在感受被迅速命名的此刻,我们希望重新提问:我们为何如此需要心理学?
今天刊发的该系列第二篇报道,聚焦心理咨询师邱雨薇,以及“自恋型人格”背后究竟回应了怎样的时代情绪与关系想象?

去年10月开播的综艺《再见爱人4》中,嘉宾杨子和黄圣依的沟通方式引发了受众热议。频繁的打断、说教、下判断,杨子习惯的表达方式让不少观众感到窒息。观察嘉宾papi酱的一句“他怎么那么喜欢给人上课、喜欢给人当爹?”精准捕捉到杨子的情感姿态带来的压迫。观众们将这种夹带优越感与控制欲的情绪倾向归结为“自恋型人格”的典型表现。
“NPD”(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的缩写,由于涉及到临床诊断性,文内以“自恋型人格”代替流行语言中的“NPD”)一词随即登上热搜,“他是不是 NPD?”成为了网友们乐此不疲的心理诊断游戏。专业术语“自恋型人格”迅速被社交语言消费,变成一种流行的情感标记,轻易地被贴在失败关系中的某一方身上。
在网络玩梗之外,“自恋型人格”标签的广泛传播或许揭示了一种更深层的情绪共鸣——我们都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这个时代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自恋”者。以美国乔治亚大学心理系教授W.基斯・坎贝尔为代表的心理文化学者将近半个世纪定义为一个被自恋文化挟裹的“自恋时代”。在今天,“自恋”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精神气候,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人的自我体认,以及与他人建立联结的方式。

付金涛 译
后浪·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09
从业以来,心理咨询师邱雨薇一直关注“自恋型人格”的相关议题,为相关受害者进行心理咨询,并主持播客“邱后算账”与“亲爱的勇敢者们”,为更多人提供公共交流、彼此照见的平台。
她发现,当代中国与坎贝尔写作的时代共享着相似的文化语境。新自由主义与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社会结构性问题与信息爆炸的合谋,让越来越多人困囿于封闭的自我,拒绝同他人实现理解。
什么才是健康的自我价值感?它与病态的自恋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当不得不与一种笼罩性的“自恋文化”共处,我们该如何辨识关系中那些隐秘的操纵,又该如何想象一种不再被自恋逻辑主导的、更有活力的关系形态?这可能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共同面临的难题。
01 认识自恋型人格,要超越病理化的视角
古希腊神话中,美少年纳西索斯(Narcissus)临水自观,沉溺于自身的水中镜像,最终孤独陨殁。纳西索斯的故事在后来成为“自恋”的经典隐喻:当爱的目光仅仅折返于自我的完美想象,周身所有意欲靠近的触手都被轻蔑地隔绝,“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我”本身,都会变成贫乏脆弱的幻影。

相较于“NPD”一词作为流行语在中国互联网语境中的迅速发酵,纳西索斯成为自恋者的象征,历经的是一段缓慢的来路,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专业化的历史紧密相关。1898年,英国医生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首次将“纳西索斯倾向”(narcissus-like tendency)引入进心理描述。20世纪初,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进一步系统化了“自恋”理论,启发我们:当爱的能量无法指向他人时,将回流至自我,滋生一种病态的幻想结构,让个体逐渐失去与现实世界的联结。
虽然精神分析在科学主义潮流中被遗留在了历史的边角,但“自恋型人格”依然被纳入主流心理学的临床诊断之中,过度的自恋被定义为一种病理表征。《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明确指出,“自恋型人格障碍”是一种缺乏同理心的普遍心理行为模式,依据不同的测量标准,自恋型人格障碍在人群中的平均患病率为1.2%-6.2%。
这一定义中的“同理心”引发了邱雨薇的思考。将自恋型人格障碍定义为同理心的“缺乏”,暗示着一种先天的失能。但从来访案例中,邱雨薇意识到自恋型人格也许并非天然匮乏感受他人的能力,而是擅于随时撤回他们用以表演关心与理解的同理心。

当蓓儿走进心理咨询室时,邱雨薇在她身上觉察到了艰难的挣扎。那是一次“断崖式”分手,让蓓儿几乎丧失了自我判断的能力,以至于她“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让他对我的印象大打折扣”,“时常搞不清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我不够好”。
难解的困惑源于伴侣前后殊异的态度。在关系前期,伴侣对她一见钟情,迅速开启了热烈的主动追求,而当蓓儿分享了自己不符合前任婚恋观点的思考,对方的态度迅速变得冷漠,大吼大叫着数落蓓儿的种种“罪状”。这种反差巨大的亲密体验,让蓓儿在关系中迷失,分不清谁才是那个“有问题”的人。
“很多人以为自恋型人格是欠缺共情能力的人,但并非如此,”邱雨薇指出,“蓓儿的案例表明,关系前期自恋型人格非常善于营造气氛、推进关系,这些都需要同理心的调动。”
问题在于,在面对冲突时,自恋型人格的同理心迅速收回。他们看似共情,实则操控;渴望亲密,却拒绝真实;他们需要伴侣顺从依附,无法忍受伴侣成为自己。当自身利益受到挑战,自恋型人格只会以忽略、暴怒、欺骗的方式面对问题,这是正常的“自恋”与作为一种症候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区别。
在这个意义上,自恋型人格不能被简单归结为个体的病理缺陷。应该考量在个人利益遭受冲击的一瞬,是怎样的社会文化心态让自恋型人格下意识地以伤害替代了协商。拥有心理学与社会学双重学术背景的邱雨薇沿着心理学临床化的历史洄游,重拾弗洛伊德于历史深处的提醒:了解一个人的心理模式,需要剖析其成长历程中的隐秘创伤,且私人的创伤必然植根于更宏观的社会症候中。

因此,在2024年出版的《恋爱中的暴君》一书中,邱雨薇强调,对自恋型人格的反思不应止步于如何“识别”这类人格类型,更应该继续追问,自恋型人格为何会在当代社会中如此频繁地被激活?它背后究竟回应了怎样的时代情绪与关系想象?
只有松动那些被病理化的“天性”或“缺陷”,将结构性的视角纳入对个体关系的反思,才能迎来更彻底的解放。
02 匮乏的情感教育与难解的性别阶级困境
“没有爱能流出我的身体”。在英剧《去他*的世界》中,主角詹姆斯这样形容自己。詹姆斯曾目睹母亲自杀的场景,且与父亲几乎没有情感交流,靠虐待动物来验证自己是否还拥有“感觉”。仿佛只有在施展暴力的瞬间,他才能模糊觉察到那种名为情感的冲动。直到与少女艾丽莎意外结伴踏上一场逃亡公路旅行,詹姆斯才得到了人生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启蒙,感受陌生的温流在心中化开。
《去他*的世界》是一部真空的童话。长期缺失的情感教育在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冒险旅途中实现,危险和意外逼迫詹姆斯迅速成长,但家庭和社会教育系统仍然失语,无力回应詹姆斯和艾丽莎的未来。回到现实,邱雨薇提醒我们注意,滞后的情感教育系统与不平等的性别、阶级结构合谋,正深刻地影响着“自我”的形成,让自恋和情感压抑成为了与男性气质紧密捆绑的特质。

邱雨薇认为,从生理角度看,男性和女性出生时在情感需求上并没有本质区别,但美国医学博士希妮・阿姆巴达尔(Sheenie Ambardar)的研究表明,被诊断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中,男性的比例是女性的3倍,这是因为“男性长期习得的是压抑情绪,而非处理情绪的能力。”
西方社会自90年代开始尝试通过“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来修补青少年的情绪教育缺口。相关理念2011年才在中国教育体系中露面,且难以穿透深层的性别期待,“男儿有泪不轻弹”、“要像个男子汉”等文化叙事持续地固化着理想的男性形象。此前曾被广泛讨论的“男孩教育危机”正暴露了教育体系对男性气质的潜在要求,“阳刚之气”成为强加于男性身上的隐形盔甲。
邱雨薇的社群成员万万仍然记得,小时候的自己不习惯大声说话,被同龄人讥讽为“娘娘腔”,甚至被老师在公开场合羞辱为“恶心”。当他不解于这样的评价,试图找父母印证,迎来的却是攻击的再一次复制:“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密不透风、单一严苛的评价体系从学校延伸至家庭,让万万直到现在仍感觉自己所有的自信只是一种“伪装”。“脆弱”、“悲伤”等情绪虽早已被排斥出他的表达系统,却一直潜伏在心室深处,如沉默粘稠的藤壶。
社会倾向于以高度工具化的方式定义“成功男性”:一个“好男人”无关其是否擅长沟通、敏感体贴,而是关于是否“事业有成”。情绪被视为效率的负担,感知力成了不合时宜的累赘,于是男性被推向一种危险的断层:外在强大,内里空心。邱雨薇发现,“当男性不用承担表达和处理情绪的责任,只需要对外在评价负责,这样的标准会成为一把双刃剑——男性减少情感劳动的同时越来越走向自我压抑”。自恋型人格行为是这种结构性压迫下的创伤反应。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研究印证了邱雨薇的观察,在《改变的意志:男人,男子气概与爱》(The Will to Change: Men, Masculinity, and Love,2004)一书中,胡克斯指出,父权文化将男子气概推向了两极化,男子气概表现为或是趋于暴力,或是极度脆弱。这种二元性在自恋型人格的人格气质上有清晰的体现。
那么,是否有可能想象出一种健康完善的男性气质?邱雨薇认为这样的设问事实上颠倒了性别气质与自我教育的关联:“新的男性气质不可能由某种理论框架自上而下地强行构建。应该来自男性自身的主动反思与修复。有改变意愿的男性,可能会在探索过程中基于自身需求和情绪,借鉴对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批判,发展出新的性别气质。”她说,“这也是男性必须学会承担的责任。”
当然,自恋型人格并非男性专属。现实往往更为复杂:暴力的受害者也可能复制新的暴力。一位来访女性曾告诉邱雨薇:“我是个女性主义者,但我竟然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母亲,这让我痛苦,也让我感觉失败”。她的母亲,有明显的自恋型人格倾向。
隐秘的暴力在关系链条上不断传递,膨胀的主体对他人施加的伤害早已超出性别的划分。性别压迫不过是不平等权力结构压迫最直观的一环,继续追问结构的根源,我们终将抵达一个更基础的议题:阶级。
在“邱后算账”的一期节目中,嘉宾宇梵分享了阶层跨越的经验对自己情感的型塑。邱雨薇总结道,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广泛的阶级流动经验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了相当大部分人的生存信条。成为这一法则之下的佼佼者要求人迎合外在的评价体系,并将这种外在期待转化为对自己和身边亲密之人的压力,个人内心更隐幽的情感需求被一再遮掩。

在艰难的自我训练后,宇梵坦言:“相较于别人,我就像是赤裸上阵。于是我训练自己学会了只关心我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将自己从主流评价体系中剥离出来,是一个痛苦但值得的过程。”
这或许正是“自恋时代”的艰难一课:在一个压抑情绪、奖励竞争的语境中,真正的复原不是顺应外在评价体系自我优化,而是敢于卸下压抑情绪的盔甲、回望内在,重建真实的情感连接。
03 自恋时代的“爱无能”
重审投向自我的目光,不是为了将视力永久地停驻于自身。邱雨薇始终强调,反思自恋议题,是为了重新开启与他者相遇的可能。在她的心理咨询实践与思想写作中,亲密关系的重建成为突破自恋封闭结构的一条路径,是“自恋时代”的革命者向爱欲敞开的努力。
不过“爱是什么?”这一问题从未有恒定的答案。回望上世纪70年代至今,“爱”在中国的面貌历经变迁。曾经爱被表述为“月亮代表我的心”,理想、坚实的爱欲被整个年代信任与传唱;而90年代以后,当都市经验与市场经济裹挟个体,流行的声音是:“感情需要人接班/接近换来期望/期望带来失望的恶性循环”。爱情成为了可转移的商品,爱的主体在不稳定的情感迁徙间成了提心吊胆的“带罪羔羊”。
在诊疗室中,邱雨薇也观察到,相较于追问“什么是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爱无能”来自我标识,有关爱的建构性想象趋于失语,无法爱他人成为一种被自嘲接受的心理状态。爱与个体意志的交织在今天的变体,呈现出对浪漫爱情神话的怀疑。
这不仅是一种情绪困扰,更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症候。邱雨薇认为“爱无能”的心理状态实际上与嵌入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自恋式主体”密切相关。德国哲学家君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曾批判新自由主义下的个体自由是一种“自我肯定式的自由”,即自我需要通过否定别人来肯定自己。在现实中,这种过度强调个人主义的路径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让现代人变得既缺乏“爱的意愿”,也缺乏“爱的能力”。
“爱是一种需要意志的行为。”邱雨薇说,“它要求你走出自我,去顾及另一个人的情绪与需求。”而当下,简单的愉悦唾手可得,娱乐短视频、即时性社交让太多事情变得过于轻松,以至于很多人都不再愿为了理解一个人而付出努力。同时在过于强调效率和竞争的处境中,人们更倾向于把亲密关系也纳入一种市场逻辑来运作。
邱雨薇的观察揭露了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市场逻辑与技术工具的共同运作下对现代人的亲密关系体验的革新。正如文化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斯(Eva Illouz)利用“情感资本主义”一词中所描述的那样,现代社会的情感早已被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深度塑形。我们与谁相遇由算法决定,如何表达情绪受制于界面设计,“自我认知”则通过数据画像来完成。爱再也不是神秘难解之物,而是被不断切割与编码的数据流,亲密关系成为一种可度量、可替换的体验。
据中国青年网2021年的调查,中国89%的青少年使用过交友软件。疫情之后,线上婚恋交友软件的市场估值大幅度提升,三年间从2020年的51.3亿元攀升至2023年的93.8亿元。在今天,线上交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关系交往模式。在信息淘洗的竞赛中,每个人都成为别人眼中的参数化对象,也渴望成为被挑选的“最优解”。

但邱雨薇强调,尽管交友软件提升了筛选的效率,却也带来了一层危险的逻辑倒置。种种标签让自我成为公开展览的商品,方便他人筛选,也让人不断产生“总能找到更好的”的幻觉,以至于人们只关注爱的对象是否符合自己的筛选标准,而忽略了对自身爱的能力的训练。“当亲密关系被化约为‘匹配’与‘符合’,爱便不再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关系,而是一场利益驱动的交易行为”。
“可关系的建立从来不只是匹配那么简单,它需要艰苦卓绝的经营,需要不断的投入、磨合与调整。”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来,自我的边界充满弹性,是不断在关系中被塑造与调整的。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关于“我是谁”或“我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我是否能与他人建立平等、尊重的连接”。
正是在这里,“公平”成为对抗“自由”话语的重要维度。邱雨薇提醒,那些拥有更多社会文化资源的人,往往也拥有更多的情感选择权,例如在多元关系实践中,更高阶层的男性往往拥有更大的选择范围,这使得自由本身成为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

因此,相较于追求自由,“公平”才应当成为一段关系努力的方向,这要求关系双方愿意留在场中、持续倾听彼此、不轻易抽身。这样的练习不是顺从外部期待的“自我优化”,而是一次次踏实勇敢的驻留,一次次在喧嚣中为他人腾出空间的冒险,虽然艰难,却是在爱情神话失魅之后,对“爱无能”痼疾的有力抵抗。
那么,当经历如此艰苦的情感劳动之后,我们最后获得那个名为“爱”之物带来的回报是什么?
面对这个问题,邱雨薇沉思了片刻,然后轻声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我相信答案因人而异。对我来说,爱让我能够超越眼前的痛苦,让我相信自己不孤独。当‘我’变成了‘我们’,‘我’开始相信自己有更多可能,也能够为他人带去力量。这样的意义感是无可替代的。”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当下的心理学热?
邱雨薇:“心理学热”说明人们对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渴望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是一件好事情。同时,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目前心理学和资本化运营绑定在一起,可能会通过制造某些概念或者引发情绪去促进消费,使人被算法操控,变得越来越焦虑,背离了心理学“认识你自己”的初衷。作为消费者,我们需要用批判性的视角去看待所接收到的内容。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心理学会把责任都推给个人,仿佛社会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邱雨薇:主流心理学是受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去背景化,关注个体的改变,缺少结构性视角。这确实是心理学被诟病的一点。心理学也有把个人-社会相结合的跨学科尝试,比如:社会心理学、社区心理学、解放心理学、去殖民化心理学等。我自己在近些年在理论建构和实务工作中希望把“自恋”这个议题放在更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去理解,不仅包括个人、关系的层面,还有阶级、性别、民族、国家的视角。
界面文化:你如何理解年轻人在“躺平”与“内卷”间挣扎?你会如何建议?
邱雨薇:这背后表现出来的是在这个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个体的选择问题。传统的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可能不再适用于当下高速发展的环境。我们如何接受并回应时代的发展?这需要我们关怀自己的身心健康,打破对于既定路线的执念,结合自己的需要。
界面文化:“韧性”总被拿来描述个体如何抵抗冲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你觉得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如何维持一种不被打散的韧性?
邱雨薇: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韧性”意味着个体能够有自己的锚点,并且能更灵活地适应社会的变化。“韧性”不是不受冲击,而是当受到冲击后,按着自己的节奏来,获取有效的信息和资源,调整好状态,然后再行动起来。
“韧性”不只关乎个人的能力,也是联结更多的人,建立支持系统,打破原子化的状态。
坚持自己所热爱的,慢一点也没关系。
界面文化:很多心理学词汇比如原生家庭、MBTI人格、自恋型人格……都非常流行,怎么看待人们依赖各种术语给自己或他人贴标签的趋势?
邱雨薇:“贴标签”在创伤疗愈的初期也被称为“命名”,也就是通过掌握一个框架,帮助我们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更好地赋权个体,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随着个人力量感的提升,依赖“标签化”的方式无法看到个人的议题和关系的动态,就需要有更复杂的视角看问题,打破“非黑即白”的模式。如果过度依赖标签,不仅不会帮助我们进一步地了解自己,还会陷入“自我应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用“标签”去定义自己。比如:我是个自恋型人格,所以我就可以继续在关系中虐待伴侣。
界面文化: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经验,在你感到混乱或失衡的时候能让你平静下来?
邱雨薇:如何应对情绪压力是很重要的技巧。因为在混乱或失衡的状态下,我们会习惯性地通过解决问题去缓解情绪。可是,当这个问题难以一下子解决,很可能就会陷入到失控的状态里,难以集中注意力做事情。我们可以通过:觉察情绪、命名情绪、看到情绪背后的需要并满足需要,这个流程来应对情绪的挑战。
情绪不是敌人,而是协助我们完成事情的重要帮手。它联结内在-外在,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出改变。比如:在工作中,我对工作合作方处理问题的方式有强烈的情绪。如果是愤怒,可能遭到了不公的对待,需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如果是恐惧,可能项目出现了拿不准的事情,需要做出进一步地调研和沟通;如果是无力,可能是压力过大,需要休息或者换工作。
本文按语部分写作:徐鲁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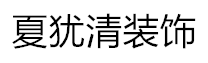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28
京ICP备2025104030号-28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